 第四十八章 紅花會 電視劇世界
第四十八章 紅花會 電視劇世界
 第四十八章 紅花會 電視劇世界
第四十八章 紅花會 電視劇世界
「挑戰我?」那弟子伸手指着自己的鼻子,滿臉愕然,隨即似笑非笑的盯着宋明鏡,點了點頭:「好!那就讓我這做師兄的,來好好指點一下張師弟的武藝。」
長須長老淡淡道:「同門較技,點到為止,切勿傷及性命。」
「於長老放心,弟子省得。」
那弟子跨出一步,盯着宋明鏡笑道:「張師弟,不要說師兄不給你機會,你先出手吧!」
這特麼功夫到不到家不清楚,高手的架子倒是擺得十足了,宋明鏡懶得廢話,身形一晃,那弟子只覺眼前一花,隨即腦門上挨了一巴掌,兩眼一翻,「噗通」一聲極為乾脆利落的昏死了過去。
現場嘈雜喧鬧的聲音戛然而止,每個人都像是被扼住了喉嚨的鴨子,發不出半點聲音來。
……
那「孫公子」一行來時六人,回返時隊伍陡增二十七人。
除了二十名老弟子以及包括宋明鏡在內的五名新弟子外,又添了兩位武當執法堂高手隨行。
一群人下了武當山,抵達官道上,才發現官道上正停着一輛囚車,囚籠四面都被黑布罩住,無法瞧清內里的情景。
圍繞着囚車,分佈着一個個清廷官兵,宋明鏡大概掃了幾眼,怕不是有兩百來人。
一眾武當弟子也是交頭接耳,低聲議論,揣測着囚車內關押的究竟是什麼人,竟需要這麼大陣仗看管。
「回廣州,出發吧!」
「孫公子」環顧一眼,說了句話,聲音清脆悅耳,隨後徑直上了唯一一輛馬車,車輪「吱嘎吱嘎」轉動起來,緩緩行進着。
有着囚車拖累,這速度自然提不起來,等到了天黑時,才不過走了四、五十里路,當晚尋了就近的村鎮過夜。
入夜。
兩道鬼鬼祟祟的身影自房間內探出頭,左右張望片刻,見無人察覺,躡手躡腳的進了「竹葉青」朱桃的房間。
不一會兒,隱約就傳出放浪形骸的嬌笑以及沉重的喘息聲,似斷似續。
青瓦房頂上,宋明鏡盤膝而坐,滿臉無語,他現在倒是煩惱自己耳朵太靈光了,特麼的想找個清靜地方安心練功就這麼難嗎?
他們寄宿在一戶小地主家,囚車就停在院子裏,四周都有官兵看守,輪流守夜。
宋明鏡忽然瞥見那紅袍番僧走到囚車旁,掀開了黑布一角,將手上一個巴掌大小的包裹塞了進去,又低聲交談了兩句,這才遮住黑布,轉身迅速離開。
而這一幕,那些官兵都似視若無睹。
「有些古怪啊!」
見此情景,宋明鏡哪還不清楚這裏面有鬼,他足下輕輕一點頂梁,人如飛燕般竄起又落下,輕盈的落身到走廊上,整了整衣衫,返回了房間。
距離廣州還遠,路上他有的是時間摸清楚情況,並不急於一時。
何況他金剛不壞神功不日就可小成,屆時戰力又增幾分,動起手來把握更大。
兩百多名隨時都可結陣衝殺的官兵,可不是幫會成員那種烏合之眾所能相提並論,加上還有朱桃,譚九公,鄧炳坤等等這一眾身手不弱的武人壓陣,宋明鏡遇上了也得避其鋒芒,不會選擇正面交鋒。
翌日天明,一行人繼續上路。
只是在那二十名老弟子中卻有兩人面色潮紅,眼窩深陷,無精打采,走起路來兩股顫顫,仿佛隨時都會倒下一般。
「怎麼?你們生病了嗎?」有與二人關係親近的弟子擔憂的問道。
「果然只有起錯的名字,沒有起錯的外號!這完全是被榨乾了啊!」宋明鏡自是心知肚明,看了「竹葉青」朱桃一眼。
倒是那位江長老看了兩人一眼,臉色立時大變,又把了把脈象,一張臉陰沉得像是能滴出水來,怒喝道:「混賬!兩個不爭氣的東西,我武當的顏面都被你們丟盡了!」
喝罵了二人,他又轉向朱桃,狠狠瞪了過去。
朱桃卻是絲毫
 無敵秒殺系統 【【2016星創獎之玄幻參賽作品】】【極致無敵流】【爆爽文】少年牧雲獲得無敵秒殺系統,笑看諸天萬界,在整個玄幻世界都留下他暴走的足跡。PS:這是碾壓流,但凡惹到一點點主角的,不管來歷,全部當遊
無敵秒殺系統 【【2016星創獎之玄幻參賽作品】】【極致無敵流】【爆爽文】少年牧雲獲得無敵秒殺系統,笑看諸天萬界,在整個玄幻世界都留下他暴走的足跡。PS:這是碾壓流,但凡惹到一點點主角的,不管來歷,全部當遊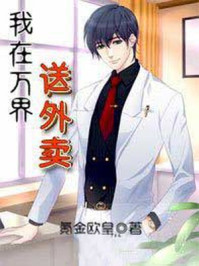 我在萬界送外賣 內容簡介:葉晨八歲那年,算命老道說:你十八歲那年將黃袍加身,天天山珍海味為伴!我信你個鬼你這糟老頭子!外賣員的黃顏色工作服也是黃袍加身?結果葉晨果真成了黃袍加身魚肉為伴的外賣員,不過……他的外
我在萬界送外賣 內容簡介:葉晨八歲那年,算命老道說:你十八歲那年將黃袍加身,天天山珍海味為伴!我信你個鬼你這糟老頭子!外賣員的黃顏色工作服也是黃袍加身?結果葉晨果真成了黃袍加身魚肉為伴的外賣員,不過……他的外 武俠世界大穿越 一位武學天賦極高的現代散打高手,穿越於各類武俠世界中,一步步成為顛峰強者的故事!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武俠世界大穿越》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薦哦!
武俠世界大穿越 一位武學天賦極高的現代散打高手,穿越於各類武俠世界中,一步步成為顛峰強者的故事!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武俠世界大穿越》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薦哦!